读《风雅颂》
这是阎连科先生在写知识分子自己“丑陋”的一步作品。小说情节看似荒诞,但现实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远比小说荒诞多了。
“我”没有选择青梅竹马,为了地位,为了事业,“我”娶了教授的女儿,赵茹萍。
然而婚后生活并不幸福,“我”追求的学术在妻子看来一文不值。她深谙世道,能“睡觉”得到的东西,就不用专研学术。“我”更像是时代的遗儿,“我”和这个时代太不合了。面对妻子赵茹萍与校长李广智的通奸,更像是“我”做错了事,“我”活的没有一个男人样,竟给茹萍跪下来苦苦求饶“不要再有下次了好吗”,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懦弱。
“我”像一个异类一样被送进了精神病院(当“权威”说你有病,你就是有病,你没有辩驳的权利)。当院长说,你不是教授吗,你去给病人讲课,当他们交头接耳,不愿听,你就可以出院了(将一个人交给“病人”来裁判时,你的认真无法逃脱这个荒诞)。“我”想着方式让病人听不懂,他们却异常认真,这时,“我”的常识失效了,“我”会进入一个死循环,“我”要逃离这里,去哪里?回家。
乡人知道“我”是“清燕大学”的教授,带着孩子争相找“我”摸头,送吃送喝,为的是孩子能考中。然而未中时,竟似盗贼样争抢我家里的东西。他们正巧撞上我后露出的一丝“羞愧”已将乡人“淳朴”的外衣撕的仅剩一件内裤了(一般作家是不敢“得罪”农民的,阎连科偏敢写出来)。
这个世界的“知识分子”是虚伪的,“淳朴”的乡人也是“丑陋”的,那还有美好的事情吗?有,那就是玲珍对“我”的爱,和四叔对“我”的恩。
“我”就没问题了吗?“我”同样有我的问题。“我”作为一个“知识分子”。能看破世俗,却又难以突破世俗的禁锢。“我”没有一个小贩活得真实,没有一个风尘女子过得洒脱。这才是“我”向往天堂街的地方。“我”看到被这个世界鄙夷的人们,竟可以活得如此真实,“我”缺失的东西,他们有(作家们常常以风尘女子作为“知音”,如果将她们的丑陋也揭露了,那作品留给人的最后一线希望都没有了)。“我”是教授啊,怎么能做这样的事。去他的教授,去他的虚伪,那些见不得人的事“我”也想做。“我”与姑娘们一起过年,无所顾忌,放肆自我。“一日不见兮,如隔三秋兮”,当《诗经》中的句子被“我”与姑娘们一起吟唱时,这就是“我”的“黄金时代”。
同时,“我”的这次放荡,造就了玲珍的死。“我”超出常人预计,同意与玲珍进行衣冠冢。当白雪皑皑的大地上,望见蝴蝶飞来时,这无法解释的一幕,是作家对现实存在的一种混沌(作者后记讲,这一幕是一个真实的情景)。
自此,“我”照顾起了玲珍的女儿小敏。她一天天长大,当有一天成人时,脸上的红晕,挺拔的乳房,真像玲珍年轻的时候。“我”喜欢上了小敏,可始终不敢对她讲出来,怎么能有这种不伦之恋。“我”怕乡人的唾弃,“我”怕世人的鄙夷。“我”将一切深埋于心,直到那一夜爆发了出来,“我”掐死了小敏的新婚丈夫(最后没有交代死没死,至于死没死已经不重要了)。
“我”开始了我的“逃犯”生活,去往“我”的精神之国,“我”寻找到了一首首《诗经》之外的古诗,寻找到了“震惊世界”的“诗城”。
“我”回到了京城。妻子剽窃“我”的书稿,拉拢关系评上了职称,过上了“梦寐以求”的生活。“我”拿着我的新发现去找李广智,李广智在与一群知识分子走“捷径”。你和“我”老婆通奸,“我”忍了。这一次“我”可是发现了一座诗城,对整个名族甚至世界具都有巨大的意义。当“我”看到李广智的与其他知识分子的集体失声,才真真切切对知识分子寄予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。知识分子你有肮脏、见不得人的一面,你对名利,对权威卑躬屈膝。但是最后你竟可以对最根本的“专业”都可以亵渎,那么就全完了。
“我”活在自我的精神世界。小说中对话的“答非所问”,“各言其说”说明“我”与这个时代完全“脱节”了,人与人的交流都有了问题。“我”回到了诗城,建立了一个乌托邦,做着“我”的坚守。这里有合大院校的老先生,名教授,这个专家,那个学者。我们抓阄,与那些风尘姑娘变着法子快乐着。知识分子中少数人的“狂欢”反衬了多数人的“落寞”。
自此,作家结束了知识分子的这场“自我审视”,哪怕写着自己都犯恶心,但却是我们当今知识分子中真实存在的。
大连
2017年12月10日
评论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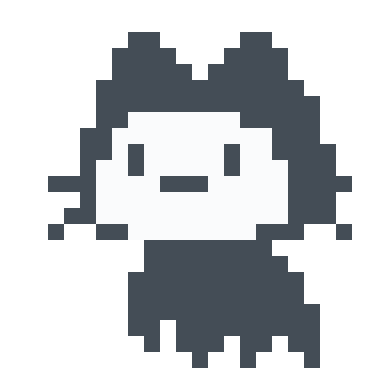 正在加载评论......
正在加载评论......